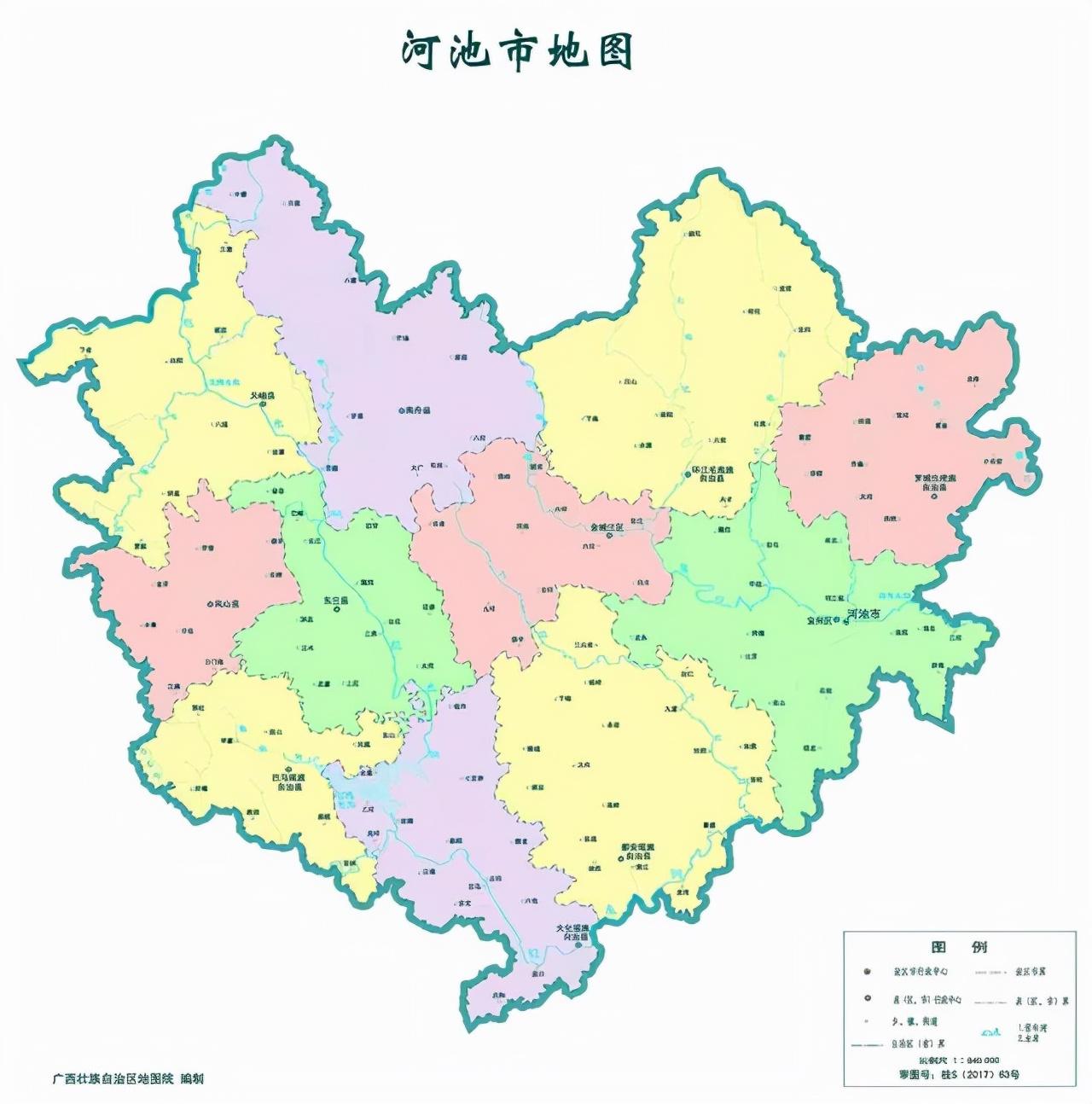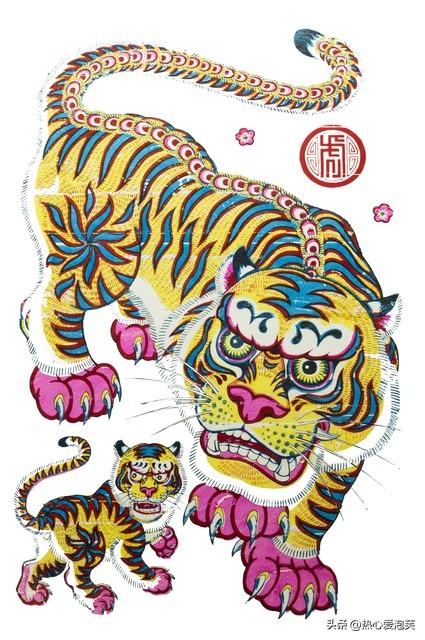十八、第二首都·奥什
从喀什出发,沿着阿乌高速G3013行至乌恰县伊尔克什坦口岸后,继续顺着公路向西跨越国境线走进瓦罕走廊,到达吉国南部的“撒利-塔什”。进而向西北方向继续行进便可到达费尔干那盆地,这里有吉国南部的第一大城市——奥什,被誉为吉国的“第二首都”。

苏莱曼山顶和奥什
史料记载显示,奥什城古名繁多。学界一般认为,“奥什”(Osh)便是古代的“贰师”,属大宛国,公元前7世纪,奥什城所在的地区属“大宛……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鳁、于窴”。《史记》中则记载“贰师有好马”。奥什城在古代曾叫作“Sutrishna”,也被称作“Usrushna”。《新唐书》中记载“东曹,或曰率都沙那,苏对沙那,劫布呾那,苏都识匿,凡四名。居波悉山之阴,汉贰师城地也”。这里的“东曹”“率都沙那”“苏对沙那”“劫布呾那”“苏都识匿”都是奥什的古名。元代汉文文献将奥什记为“倭赤”,明清时期史书中写作“鄂什”,《清史稿》中所载“北极高度”即相关地点所在纬度,“鄂什高四十度十九分”,与现今奥什城的地理纬度基本一致。
有学者从地名发音的相似性角度进行推证,认为“苏对沙那”就是汉代的大宛国贰师城。“贰”在汉代读作“rie”,“师”在汉代读作“shi”,“贰什”全读为“rieshi”。由此可见,“Sutrishna”中的“rish”与汉代“贰师”的发音相近。到了清代,“贰什”在汉语中读作“er shi”,如果以西北方言来读,则读作“e—shi”,与“Osh”的读音非常接近。此外,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可知,奥什(Osh)也可能来自“Oosh”。在柯尔克孜(吉尔吉斯)语中,“Oosh”意为“交换”。

俯瞰奥什
奥什城作为丝绸之路沿线重要城市,在历史上曾是商贸往来的重要枢纽,因此奥什地名的由来是否与其在历史上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中曾发挥的作用有关,值得进一步研究。除文献资料外,考古发掘也在分析“奥什”与“贰师”的关系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州马哈马特的明铁佩古城遗址距现今的奥什城约45公里,曾是费尔干纳盆地南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丝绸之路上的古城遗址之一。考古学者发现,明铁佩古城存在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世纪前后,其活跃期与中国历史上的西汉大体相同,应与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大宛国有密切关系。除了其所处的时代以外,明铁佩古城的地望和特征,也与中国历史文献中的“贰师”相符,据此可以推测奥什附近区域为中国古代文献所载“贰师”城。
奥什南部与塔吉克斯坦交界,北边挨着乌兹别克斯坦,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里,这里始终是中亚的十字路口,也曾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分支经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穿城而过,千百年前载着珍稀商品的驼队穿过中国新疆的荒漠,翻越帕米尔—阿赖山脉,抵达富饶的吉尔吉斯斯坦奥什绿洲,在这里稍作休整之后,继续踏上前往中亚其他城市的旅程。
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初,这片土地便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要道。东西方之间的商贸往来,促使人口流动变得更为快速和频繁。
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6世纪,匈奴、鲜卑和突厥人相继到达奥什地区,并先后在此建立政权。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的势力逐步向中亚地区扩张,先后建立了倭马亚王朝(又称“伍麦叶王朝”)与阿拔斯王朝,到13世纪中叶为止,奥什城一直笼罩在伊斯兰文化氛围中。据莫卧儿王朝的创立者巴布尔描述:“有许多传说谈到了奥什城的精彩,奥什要塞的东南方是一座比例协调被称作巴拉科的山脉,在山脉的顶端,苏丹穆罕默德建立了一处临时行宫。
”7世纪至12世纪,吉尔吉斯人在中国文献记载中被称为“黠戛斯”或“辖戛斯”。12世纪末13世纪初开始,奥什城长时间处于蒙古人统治之下,他们将吉尔吉斯人称为“吉利吉思”或“乞儿吉思”。17世纪,奥什城成为浩罕汗国的一部分,根据史料记载:“浩罕,古大宛国地,一名敖罕,又曰霍罕,葱岭以西回国也。东与东布鲁特接,南与西布鲁特接,西与布哈尔国接。有四城,俱当平陆。”18世纪,俄罗斯帝国向中亚扩张,奥什城进入了被俄罗斯帝国统治的阶段。
作为丝绸之路沿线重要交通枢纽,奥什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据史料记载:“自喀什噶尔往西北去十八日至鄂斯地方,平川三百余里,小城一座,大庄四处,园广田多,地界大河一道,乃自淋等处流往之水,归安吉彦。该处种田,小水九股,俱归此水,柴草俱好,南北皆山……由鄂斯再往西去七日路,至霍罕。此乃霍罕等处来各回城贸易经商常行大路。年年来往,使人不断。”这里的“鄂斯”即奥什。
如今,奥什已经发展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二大城市。曾经有朋友告诉我,奥什是一座缺乏魅力的城市,城区内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建筑和错落无序的民宅。比较吸引人的是城市中央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苏莱曼—图圣山,相传是苏莱曼的埋葬之地,每年会有很多穆斯林朝圣者前来。无论如何,来了吉国如果不去一趟奥什,终究是一次遗憾。为了不给自己在吉国的生活留下遗憾,我把奥什作为了自己回国前最后一次旅行的目的地。
前往奥什的旅行,我计划了很久,向同事和学生咨询了很多关于奥什的问题。出人意料的是,绝大多数人都没去过奥什,他们告诉我奥什有很多乌兹别克族,很危险,吉国北部的人一般都不会去奥什。奥什是吉国名副其实的古城,复杂动荡的历史将这里曾经的繁华掩埋在时间身处,历史遗迹如今所剩无几。在民族冲突与融合、边境更改与变动的影响下,奥什民族比例稍显复杂。它虽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文化中心城市,但乌兹别克族占奥什人口的比例达到40%以上。因此,奥什显得和邻国乌兹别克斯坦更合拍。碍于混乱的边境和飞地,奥什只能无奈割开与乌国的民族文化纽带关系,被差异极大又远在雪山对面的北方吉尔吉斯族所管辖。
复杂又绵长的历史,给这里带来的只有无尽的纠结与悲伤。
1990年6月和7月,在距离奥什不足55公里的乌兹根,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之间发生了一场血腥的暴力冲突,至少有300人死亡,而据更加广泛流传的民间说法,死亡人数至少超过1000人。如今的奥什市民,大多都有亲人或朋友这场暴力冲突失去了生命。这条伤痕,时刻都在考验着这座城市的稳定和发展。作为最具乌兹别克气息的吉国城市,奥什一直是国内民族分裂主义的源头。自独立以来就久经民族主义暴力的困扰,让本就根基不稳的吉国显得更加局势动荡。南部以奥什为中心的农耕文明与北部以比什凯克为中心的游牧文明分庭抗礼,这又给奥什增添了分裂的特质。
对于南北间的裂痕,国家政府一直在试图弥补,但就像那条比什凯克到奥什的南北公路一样,一直不顺畅。一年中的10月末到次年3月,南北公路由于被风雪覆盖而危险重重。其他时节,落石、雪崩、滑坡也会阻断公路。因此,这趟本来只需要7、8个小时的旅途需要十多个小时才能顺利走完。奥什与国家心脏的距离实在难以缩短。
从比什凯克前往奥什十分不易。两者之间除了飞机外没有任何陆路公共交通工具,只能再奥什巴扎和比什凯克汽车站西站附近的“包车点”与人一起拼车,完成长达十多个小时的路程,费用 1200索姆。作为贯通吉国两大城市南北公路,其路况是吉国最好的;因穿越天山山脉,它也是险峻、奇美的。清晨开车沿着南北公路从比什凯克出发,穿过城镇、农田、草原,进入天山里面一路爬升,先后越过两座海拔3200多米高的隘口,在雪山夕照里,再穿过开阔的苏萨梅尔山谷,绕过巨大托克托古尔水库,向下深入纳伦河峡谷,最终才来到宽阔的费尔干纳盆地。在平原上,穿过贾拉拉巴德和乌兹根,在深深的夜色里抵达奥什。一路风景很美,但也可以说是历尽艰辛。
我拼车前往塔拉斯的时候,欣赏了南北公路的险峻和奇美,也体验了坐车的劳累,实在没有勇气和精力再拼车去奥什。最后在马克的帮助下,买好了从比什凯克到奥什的往返机票后,我和小眠羊就动身出发了。出发当天,康哥热心地把我们送到了玛纳斯国际机场,并且告诉我在哪里办理登机牌和安检。这是我第二次来机场,上次到这里还是送武汉的朋友回国。那个时候中吉国际航班刚刚开通,回国的人非常多,我帮朋友拿着行李,送他们进了三楼的安检。

吉国飞机
到达机场时,距离登机还有四十多分钟,办理好登机牌后,我就带着小眠羊直奔三楼的安检。经过二楼办理国际航班登机牌的地方时,我回想起了送朋友去安检,自信地告诉小眠羊我们没走错,再往上一层就是安检。
三楼的安检空无一人,我直接把护照和登机牌递给了坐在岗亭内的工作人员。就在我好奇为什么安检的人是军人的时候,岗亭内的工作人员让我把牵签证交给他。此时我在吉国的签证已经过期二十多天,但是我并不出境,就没放在心上,只是疑惑为什么去奥什要查签证。工作人员拿着我的护照和签证审核了好久,然后起身离开岗亭走到了大厅最里面的办公室,几分钟后招手让我过去。
我顿感不妙,不晓得会发生什么。我到办公室后,他们的领导告诉我签证过期了。我表示新的签证已经在补办,我今天只是去奥什而不是离境。听到奥什两个字,领导让工作人员再一次确认了我的机票,这个时候工作人员才发现我是去奥什。他们告诉我去奥什在一楼安检,三楼是国际航班安检。听他们这么说,我才意识到自己走错了地方而闹出了大乌龙事件。接过护照和登机牌后,就领着小眠羊飞奔到一楼。进一楼安检前,刚才审核我资料的工作人员叫住了我俩,拿出手机拍下了我和小眠羊的护照信息,这一举动为我回国离境埋下了麻烦,让我差点儿错过回国航班。
周末去奥什的人真不少,去停机坪的摆渡车坐满了人。我乘坐的航班执飞飞机是波音737-200,隶属于吉国Aero航空公司,机身载有吉国国旗。该机型最后一架于2000年交付,机型比较老。从机身的彩绘和外观,能够看出今天乘坐的这架飞机服役时间已经很久了。
我和小眠羊的座位比较靠后,幸运的是我的座位靠窗,这样极大方便了我拍摄飞跃天山山脉时的景象。玛纳斯国际机场航班很少,所有乘客都登机落座后,我们的航班就开始推出,滑行至跑道后准时起飞。飞机向东北方向起飞,爬升至一定高度后,转弯向西南飞去,转弯的时候可以看到黄绿相间的土地和散落四处的一片片湖泊。
约莫过了不到20分钟,飞机就飞到了天山山脉上空。之前我以为天山山脉在楚河平原上是拔地而起的,从高空看下去才发现,其实天山山脉和楚河平原之间存在大片低缓的群山。这些山是平原向高山的过渡地带,在地面看的时候,很容易误以为这些山与其身后高大的雪峰是一体的。飞过低缓的群山后,天山山脉里一座座挺拔的雪峰出现在飞机下方。高空万里无云,能够清晰地看到相连的每一座雪峰,如同汉白玉雕刻的群山。雪峰之间的山谷同样清晰可见,甚至山谷之间沿山势而走的公路都能看到。


飞到天山山脉中间的时候,陈年积雪突然消失。山脉之间海拔较低的苏萨梅尔山谷悄然出现,一条公路在谷底一路向西,我确定这就是通往塔拉斯的公路。飞过一片雪山后,吉国最大的水库——托克托古尔水库出现在飞机右侧的舷窗里。向外望去,可以看到它如一颗巨大的葫芦形蓝宝石一样镶嵌在没有积雪覆盖的群峰之间。跨越最后一座雪山后,飞机就进入了费尔干那盆地的上空。
费尔干那盆地和楚河平远有着完全不同风格景象。费尔干那盆地处于农业文明地区,大片的耕地井然有序,都种上了农作物;而楚河平原则处于游牧文明地区,地上都是肥美的牧草。飞机落地前会经过乌兹别克斯坦的上空,从地面上分布的村落来看,吉国和乌国表面上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机场附近的耕地都覆盖上了地膜,缘于费尔干那盆地是中亚重要的产棉区,我猜测地膜下面种的是棉花。
飞机停在了奥什国际机场近机位,机场很小,一看便可看到航站楼的全貌。航站楼相对于马纳斯机场要新一些,但是更小,小到都没有登机廊桥连通。我走下飞机跟随着人流走进航站楼,航站楼内人很少,空荡荡的,直到走出去才看到很多司机在停车场等着拉客。

奥什机场
奥什跟比什凯克一样,可以使用打车软件和当地的地图查询软件2GIS。我和小眠羊在机场航站楼正对面写有“ОШ”的展示牌前拍了两张照片以作留念,稍作停留后就去外面的公交站坐小巴车。107路连接了奥什机场和城区,车费15索姆,大约一个小时就可到达城区。
出机场后,小巴车两边是接连不断的村子,经过一座巨大的玛纳斯雕像后,就慢慢接近了奥什城区的边缘。奥什虽然是吉国的第二大城市,但其城区面积比比什凯克要大一些。城区边缘看起来有点儿像卡拉科尔,但是比卡拉科尔更加繁华一些。街边店面林立,每经过一个公交站都有人上车。进入城区后,小巴车上挤满了人。城区和比什凯克没有太大区别,在比什凯克能见到的各类全国连锁型餐饮、超市和银行,在奥什也都可以见到,只是规模小一些。
奥什城区的建筑的确如朋友所说,大部分都停留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风格浓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四五层高的居民楼,还有一些当地人的自建房分布在城区各处。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奥什也开始出现高层建筑,建筑风格更加现代化,与比什凯克的高层建筑相比,一般无二。Ak-Buura河(白骆驼河)从城区中间流过,贯穿南北,将城区一分为二,因此城区内有各种大小桥梁连接东西。有一架名为“Dostuk Bridge”的双向四车道高架桥横跨奥什东西,是城区内最大的跨河大桥。每当交通高峰期来临,桥面总会布满车辆。站在大桥东头北京宾馆旁边,向西可以看见日落下的苏莱曼山。

列宁雕像
我们在Dostuk大桥南边的公园处下了车,在这里向东可以去奥什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向东可以去奥什国立大学,这两个地方是此行重要的目的地。五月初的奥什已经进入夏天,正午时分,阳光热烈,温度升高。公园里绿树成荫,漫步树下,十分凉爽。我们走过一座摩天轮时,我毫不犹豫地坐了上去,随着摩天轮的升高,奥什逐渐展现出它的面貌。由于摩天轮高度太低,我无法看到奥什的全貌,只看到了奥什孔子学院周边的区域,平平无奇。我和小眠羊在公园旁边的一家餐厅解决了午饭,奥什的物价没有比什凯克的高,同样的一个汉堡,便宜10索姆。午饭过后,我们马不停蹄地就去了公园对面的奥什国立大学。

奥什国立大学
奥什国立大学坐落在苏莱曼山西边。三层高的主楼是苏联建筑风格,主楼上方中间是白色柱子撑起的三角屋,屋顶底座写有金色的大学名字。整栋楼主色为正红色,辅以白色线条进行装饰。主楼前方的喷泉前,立着“I♥OSHSU”几个字母。我们来的时候正是周末,大学里空无一人,主楼前的大门紧闭,只有侧门是开着的,想进入大学内就只能从侧门进入。
几名身穿绿色学位服的毕业生正在附近拍照,我们走到侧门询问保安是否可以进入,奈何保安听不懂英语,也听不懂俄语。恰巧遇到了一位英语老师,她问我们为什么要进去。得益于我虽已到而立之年却看起来依旧二十出头的脸,我假装成留学生,告诉英语老师我们即将到奥什国立大学留学,想提前进去参观一下。在英语老师的帮助下,我们成功进入大学内。校内除了主楼也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建筑,我们看了看主楼前奥什国立大学的发展历史展牌后就走了出来。
苏莱曼山就在奥什国立大学后面,它并不算高,不足200米,周围也没有其他山脉,只是平地上突兀地隆起五个山包。相传它以穆斯林先知的名字命名,从那时起,这个地方就具有了神圣的意味。对中亚的穆斯林来说,苏莱曼山是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圣地,被奉为“圣山”。

火之门
我们从大学侧门出来后,直奔苏莱曼山。通往苏莱曼山的路就在大学后面西北角的十字路口西边,路边有一个棕色的路牌。苏莱曼上的大门是一座拱形的石头门,石头门的中间形似火焰苗,此门又被叫做“火之门”。大门外面坐着三四个向来往的人行乞的戴着头巾的大妈,其中有一人还抱着孩子。当你施舍过后,他们会捧着双手为你祈祷祝福。再往里走,就是售票处,成人票价20索姆,孩子是10索姆。买票后,就可以开始登山。山脚下是一座圆顶方形凉亭,凉亭四面雕刻着伊斯兰风格的花纹。从凉亭开始,拾级而上,就能到达山顶,这是通往山顶最为便捷的一条路。在山的西南方,也有一条通往山顶的路,路线稍长,但
坡度较缓。

苏莱曼山
最便捷的登山路也是坡度最陡得的,没走几步我就发现坡度陡增,不得不扶着山路边上的扶手往上走。小眠羊因为恐高,还未到半山腰就不再向上爬,转身走到山脚。我爬到半山腰的时候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不得不在半山腰的平台上休息一会儿。来往的登山人看到我都投来好奇的目光,几个孩子问我是韩国人还是中国人,当我说出“中国人”三个字的时候,他们就会告诉身边的人这里有中国人。站在半山腰能够看到奥什北边和东边的城区,大片的居民区一眼望不到边,接连不断的自建房屋顶密密麻麻。若不是耸立在居民区的高层建筑,奥什看起来当真有点儿像大农村。红色的奥什国立大学全貌展现出来,在整个奥什城区,它都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从山脚到山顶,我用了差不多半小时。山顶不大,有一个人造的平台在山顶外围,栏杆包裹住整个山顶以保障人们的安全。站在平台上能够看到大致呈南北带状分布的整个奥什城区。我原本以为奥什地处费尔干那盆地,四周应该都是平原,站在山顶才发现,奥什西边其实是低缓的山脉,天际线的尽头处,是帕米尔高原的雪山,令人生畏又充满诱惑。
平台上的人很多,都在这里与奥什一起合影。山顶树荫下的石头上,坐满了刚刚登上山顶休息的人们。平台对面原本是一处洞穴,以莫卧儿帝国的开国君主“巴布尔”命名。如今以改洞穴为基础建成了一座祷告室,内壁纯白,刻满了充满宗教色彩的花纹,地上放着两条地毯供来此祷告的人们使用。祷告室后面是我前面所说的另外一条上山的路,沿着这条路也可以下山。下山时会经过几处已经磨的光滑的巨石,有人从巨石上滑下。当地人信奉,从石头上滑下来能够消除身体里的病痛。
我没有选择从另外一条路下山而选择了原路返回。上山容易,下山难。等走到山脚下和小眠羊会合后,我的小腿开始酸疼。休息片刻后,我们原路返回到下车时的公园。在这里,我们才能把爬山后的暑热全部消散。午后的公园里,人影散乱,小路连边都是各类小商铺,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来这里消磨夏日午后。
暑热退去后,我们沿着奥什国立大学前面的街道步行到了奥什市政府广场。奥什市政府大楼和比什凯克国家政府大楼相似,只不过建筑规制没有那么高。政府大楼对面是经典的列宁挥手雕像,大小可以和阿拉套广场的玛纳斯雕像相媲美。在政府大楼旁边的公园里,我遇到了六个中国人,走上前向他们打听奥什哪里有比较好的酒店和餐馆。他们都在奥什生活很久了,都在私人的公司里面打工,觉得在奥什生活简单,回国发展反而压力很大。

傍晚时分,我和小眠羊打车回了奥什国立大学附近。我们感觉大学周边比较繁华,生活便利,几家像样的酒店基本都在附近。我原本入住Grand酒店,但等我到前台订房时,却被告知已经满房。无奈之下,我和小眠羊沿着Dostuk大桥,穿过桥下混乱的巴扎,走到了北京宾馆。我在吉国其实并不喜欢入住中国人的酒店,不仅价格和服务不对等,而且入住的人也都鱼龙混杂,很难保证安全。北京宾馆也是如此,我走进大厅时,坐在大厅的几个中国人上下打量我的眼神让人如芒刺背。宾馆的房间里充斥着一股灰尘的味道,从桌子上的落灰可以看出已经很久没人入住,也没人打扫卫生。进入房间到第二天退房,我的外套都没有脱下来。
办理好入住后,太阳西垂。我的房间窗户朝西,正好可以看到日落下的苏莱曼山和车水马龙的Dostuk大桥。苏莱曼山的安静和Dostuk大桥的嘈杂让我暂时忘却了对房间卫生的不满,锁好房门后便出去和小眠羊解决晚饭。
北京宾馆对面有很多家餐厅,我们对这些餐厅都提不起兴趣来。在路边一个卖水果的大妈的推荐下,我们走进了一家当地餐厅,大妈竖着大拇指告诉我们这家餐厅“欧青哈拉少”。看到菜单的一刻,我就开始怀疑大妈的饮食口味。趁着服务员接待其他客人的空隙,我和小眠羊溜了出来,在大街上凭借我们自己的感觉选择餐厅。
在孔子学院西边的街上晃了半天,我们始终不知道吃什么。我在地图上看到了熟悉的Navat,我俩不假思索地决定打车去Navat。到了Navata,我们坐在了室外的卡座上,奥什凉爽的夜风拂面而过,给人以轻松和自在。我们点了两串烤肉、乌兹根抓饭和过油肉拌面。经过一天的奔波,在入夜的时候,吃一顿丰盛的晚餐,安逸遍布全身。
再回到酒店时已经晚上十点多,我俩约定好明早一起去看苏莱曼山的日出。在对日出的期待中我和衣而卧,慢慢睡了过去,但总觉得睡得不踏实,感觉房内有人盯着我。我以为是认床的毛病又犯了,神经紧张导致我胡思乱想,难以安枕。
凌晨4点半我就醒了,打开窗户,外面清冷的风吹进来才感觉到一丝轻松。收拾好东西后,我去敲小眠羊的房门。5点半日出,5点我们就要出发,这样才能不耽误在半山腰看日出。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俩全副武装走到宾馆门口的时候发现大门是锁上的,根本出不去,看日出的计划就此泡汤。回到房间,刷手机到早上7点宾馆开门时,我俩才退房外出。
入住时小眠羊跟我说她隐约记得奥什的一家宾馆不久前发生过命案,不晓得是不是北京宾馆。我坚定地告诉她肯定不是,我记得是上海城。退房后,好奇心驱使着我去搜索“奥什中国人命案”的新闻,看到“北京宾馆”四个字,我感觉霉运上身,小眠羊也有同样的感觉。吃完早餐后,我俩决定再去一次被当地人称为“圣山”的苏莱曼山,消除身上的霉运。

苏莱曼山博物馆
这次登山我们选择的是苏莱曼山西南方向的登山路线。路线开始于山脚下的一座停车场,起初登山的路就是公路,可以开车上去,直抵山上的博物馆。
从山下看上去,苏莱曼山博物馆就像是一只镶嵌在半山腰山体内的大碗。它建在圣山上一个被苏联炸开的山口上,里面又通向一座洞穴,落日时分看上去就像一个淡色素雅金属巨碗缀在如红色宝石般的山体之上,仿若外星文明在地球的对节点。博物馆位于洞穴之中,由两个独立的楼层组成。进入博物馆需要购买50索姆的门票,从门口进去就是博物馆的一楼。
一楼是主要的展示区,由于是依托于特色洞穴来展览布局的,所以灯光十分昏暗,在一些“简陋”的各式洞穴空间里,散布陈列着陶瓷碎片、古老的砖石工艺、岩石和一些脏兮兮的动物标本,还有一些本地几千年最原始的萨满教文化展览,更让人感慨这里的历史绵长与神秘气息。而从二楼由天然洞穴改造而来的窗口向外望去,则能够看到奥什南边的城区。从二楼出来,是一个大平台,几个孩子看见我脖子上挂的相机,想跟我一起拍照。我招呼他们站在一起,以奥什南城为背景,拍下了一张照片。

从半山腰的博物馆继续往山顶走,仍旧需要花费20索姆购买门票。通过检票处后,就能看到远处山顶上飘扬的吉国国旗。通向山顶的路十分平缓,就好像是架在山顶和博物馆之间的吊桥,空间宽阔,走向山顶的时候还会经过几块除灾消病的“圣石”。我有心体验一次从“圣石”上滑下去,不料小眠羊恐高的厉害。即便是上山的路如履平地,她看到百米之下的奥什城区的时候依旧恐高。我们只好放弃继续向上爬,转身走回山脚下。
没能接触“圣石”,北京宾馆带来的心里的霉运依旧还在。我和小眠羊从苏莱曼山的西南门绕到火之门,把两百索姆交给了坐在地上行乞的大妈,希望她们的祈祷和祝福能消除霉运。
走到奥什国立大学后面的大街上已经是正午,我们在附近一家还不错的西餐厅吃了烤虹鳟鱼后便在街边遛食儿,去机场之前再感受一下奥什的平淡。大学西边的十字路口处,有一家人满为患的冰淇淋店,好多人坐在街边的长凳上吃着冰淇淋。我和小眠羊被他们吸引,跟在人群后买了两个店里最贵的冰淇淋,那独特的开心果风味,我回国后依然记得。
我们的飞机是下午五点多,因我想要上厕所而找厕所未果,我们提前打车到了机场,到机场时前序航班刚从玛纳斯国际机场起飞。去机场的路上,我又把奥什的街道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我知道,这一走可能就没有机会再来奥什了。
回去乘坐的飞机是一架ATR螺旋桨飞机,这么小巧的飞机还是第一次坐。从奥什国际机场起飞没多久,就进入了天山山脉的上空。不巧的是,高空多云,飞机一直穿梭在云层里,天山山脉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实在太累了,没一会儿就睡着了。快到比什凯克的时候,一阵剧烈的晃动把我惊醒。飞机遇到了强气流,随着飞行高度的降低,晃动越来越严重。我勒紧安全带,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情况,只看到地面昏黄一片。等飞机颤颤巍巍地降落在跑道上,我才知道地面刮起了沙尘暴,大风裹挟着风沙从哈萨克斯坦吹来。
出机舱的一瞬间,很多人的帽子都被吹飞,地勤工作人员和乘客追着帽子跑。我顶着大风走上了摆渡车,摆渡车几乎围着停机坪绕了一圈才停在了航站楼门口。下摆渡车的时候我跟小眠羊说真不想离开机场,恨不得直接在机场坐飞机回国。出了航站楼,我们在停车场坐上了到市区的GOBUS小巴车,每人250索姆。
小巴车驶出机场的时候,我看到了道路两边是挺拔葱郁的白杨树。已经长出新叶的杨树,彰显着中亚春末夏初的生机。南边的天山依旧在薄云翻腾中若隐若现而不失巍峨,绵延上千公里。上次看到这样的景象还是两年前,当时回国无期,而这次再有半个月就可以回国了。
在吉国的最后一次旅行,以苏莱曼山的初夏而结束。
后记:
从奥什回到比什凯克半个月后,我登上了回国的航班。
去奥什时,我在机场因走错地方而接受了护照和签证的审核。回国从海关出境时,边检员查到了我的信息,拿着我的护照和离境签审核了很久。他打电话叫领导来的时候,我内心彻底慌了,害怕因离境签不合格而无法出境。领导用英语问我一个人回国后,我的妻子怎么办?这个问题让我匪夷所思,我告诉他我未婚。领导问跟我一起去奥什的女生在哪里。听他这么说,我恍然大悟,告诉他小眠羊是我的朋友,她还要继续留在吉国工作。
领导和边检员解释一通之后,边检员才不情愿地在我的护照上盖上了出境章。得以放行后,我飞奔到登机口才赶上了最后的登机。进入机舱坐下,听到南航空乘的问候,我才彻底安心。
执飞CZ6006航班的飞机升空之后,在机场上空绕了半圈,然后向东边的乌鲁木齐飞去。我看到了玛纳斯国际机场的全貌和远处云雾缭绕的比什凯克。
此去一别,注定是经年不见。

我在吉尔吉斯斯坦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