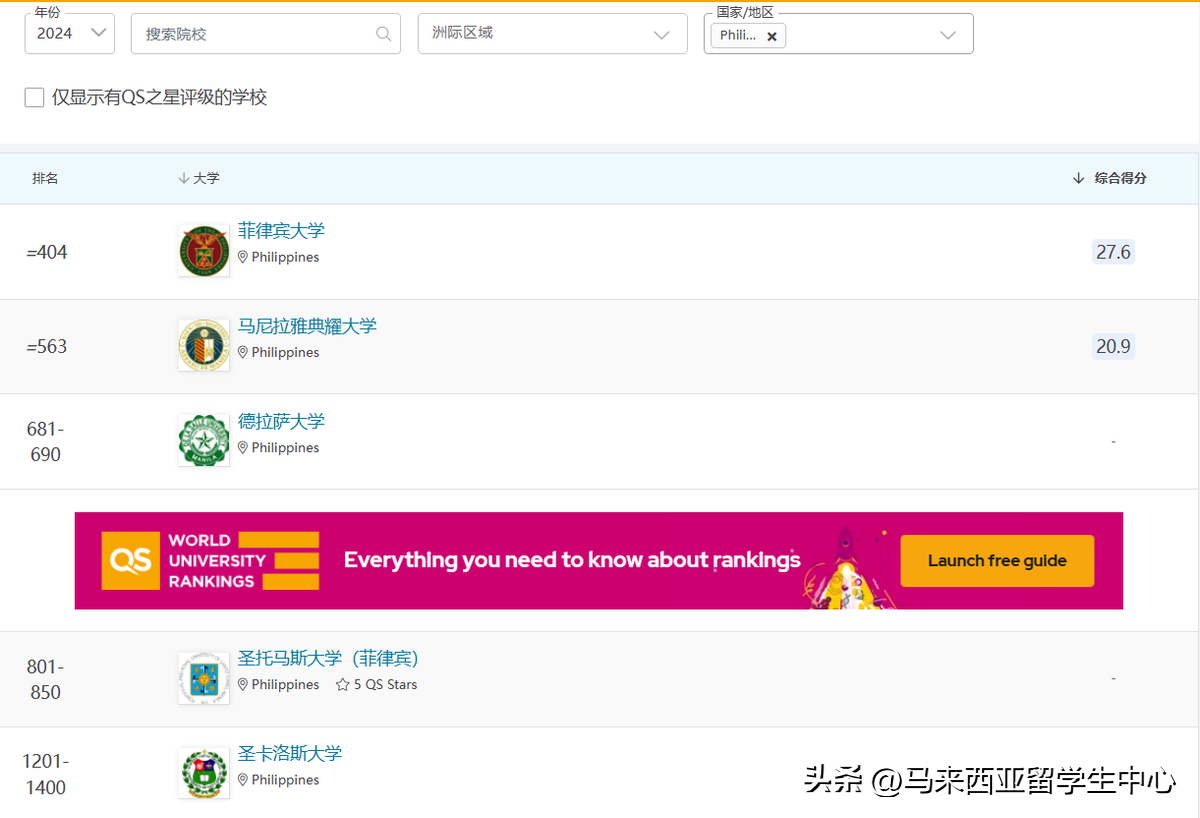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入宋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曾祖陶侃为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与王导同列,因出身寒门,而被世族讥为“小人”。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父陶逸做过安城太守。陶渊明二十九岁时任江州祭酒,因不堪吏职,不久即辞职归里。三十五岁时做桓玄属官,三十七岁时居家躬耕。四十岁时为刘裕镇军参军,四十一岁时为江州刺史刘敬宣建威将军参军。义煕元年(405)八月为彭泽令,十一月弃官归隐。史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宋书·陶潜传》)此后一直生活在庐山脚下农村,再也没有重返仕途。

陶渊明,并不是生来就要做隐士的。
东晋士人儒、玄双修、“随事行藏”、既依顺自然又不违名教的人生取向,对陶渊明也有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在他年轻时对人生道路的思考上,反映在他的思想修养、性情、志趣上,也反映在他的仕而复归上。
早年的陶渊明,对不违名教和依顺自然的人生态度都是肯定的。所谓“履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认为遁世以独善其身或入世以大济天下,只要合于人的本分就好。所谓“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感士不遇赋》)。

基于这种认识,早年的陶渊明,一方面不断加强儒学修养(《饮酒》其十六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事无成”),树立远大的志向(《杂志》其五谓“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对功名事业无限向往,以至中年不改此心(《拟古》其八谓“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
另一方面,他也遍读包括老、庄著作在内的“千载书”,向往羲皇之世。“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书》)同时,养成了喜爱丘山、厌弃世俗之事的气质(“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和不以贫贱为念的心态(“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

陶渊明早年的思想修养,实可用他的两句诗加以概括,即“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拟古九首》其八)。他主要是用伯夷、叔齐“绝景穷居”、“采薇高歌,慨想黄虞”那样的“贞风”亮节和荆轲志在功名的奋斗精神,来培植、滋养其灵魂。这种孕育着两种人生取向的思想修养,和东晋名士为适应合名教、自然为一的人生方式所作的儒、玄双修,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可以说,渊明很早就受到过儒学、玄学人生观的影响。
陶渊明一生曾三度出仕,尽管他说做官是因为“家贫”、或为归隐攒一点资金(所谓“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最大的目的,还是想在建树功业方面有所作为。也就是说,他的再三出仕,正是他早年就有的儒家入世的奋进精神在起作用。如果一切如意,他是会奋斗到底的。

可惜他生活在晋、宋易代的时期,乱、篡相继,他不但难以实现政治理想,而且极易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的常恐罹谤遇祸、忧心忡忡,绝不亚于当年的阮籍。既然“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鸣惊”(《感士不遇赋》),“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与子俨等疏》),于是便彻底做了“逃禄而归耕”的“达人”(《感士不遇赋》)。
显然,陶渊明最后一次逃禄归耕,固然是因为时不可为,是为了全身远祸,但交融其中的还有他的“质性自然”(《归去来辞序》),或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即早年就有的依顺自然的人生取向在起作用。其实,这也是促成他前二次仕而复隐的重要原因。不然,他一边做官,一边深切怀念林园、念念欲归,就不好解释。

从人生取向的角度看,陶渊明的归隐,的确是依顺自然的情绪起了主要作用。但归隐之后,他的入世之心、功名情结并未冰释。不然,他怎么会发出“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那样的慨叹之音(《杂诗》其二)?怎会写出“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那样“金刚怒目”式的诗句?要之,他早年就有的两种人生取向,始终影响到他的人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只是随着所处形势的不同,占主导地位的人生取向有所变更而已。
彻底归隐之前,陶渊明的人生境界和审美趣味,较之东晋士人(包括口唱玄音而又热心功业的名士)并无大的区别。彻底归隐之后,才进入一般名士无可企及的人生境界,并形成与其人生取向一致的审美趣味。
其人生境界,简言之就是贴近自然、融进自然,与道合而为一。他能达到这种人生境界,自与他所坚持的人生态度、人生方式有关。

最能反映陶渊明人生态度的诗歌,莫过于他的《形·影·神》。其中,《形赠影》说人生不如大自然长久,求仙以得长生又做不到,那就饮酒求醉好了。《影答形》不赞成“形”提出的求仙、饮酒说,而以追求功名为人生目标。《神释》则谓人皆有一死,既否定“形”提出的饮酒说,又否定“影”提出的功名说。而说:“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显然,“神释”云云实为作者之言,表明他追求的是依归自然、融进自然、与道合一的人生境界。他讲的“委运”、“纵浪大化中”,既是对人生境界的描述,也是指达到这种人生境界所应采取的人生方式。从理论上讲,其人生取向与道家(特别是庄子)、玄学家的主张并无两样,但从实践的角度看,渊明的人生方式和庄子、玄学家都很不同。
他们的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渊明能坚持做到委运顺化、与自然合一,主要靠的是儒家的传统观念和佛家般若思想,与庄子和玄学家只是一味讲体道而行、逍遥无为,与道合一,是不同的。
由于早年本有两种人生取向,归隐之后,功名之心并未彻底泯灭,加上对时变的感慨,对世无知音的寂寞感、孤独感和“闲居寡欢”的苦闷,对人必一死的无可奈何,以及生活的贫困,都使他无法以宁静之心去委运顺化。他所面临的矛盾、痛苦,仅靠醉饮是不能消除的。于是便用儒家先师的遗训告诫自己,用先贤安贫乐道的人格、高士绝景穷居的遗烈、君子固穷的操守勉励自己,用佛教讲的一切法相皆虚幻不实化解功名情结、排除忧生之念。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强化归隐之心,一次又一次摆脱干扰,直到进入与自然合一的人生境界。
二是陶渊明与自然合一的人生境界,是在田园生活中,通过从事诸如饮酒、弹琴、吟哦、耕作、和亲友叙旧、和邻里议论农事等平凡的日常活动创造出来的。
庄子和玄学家主要是通过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来达到与道合一的人生境界,具体显现为精神活动。陶渊明与自然合一的人生境界,则不但显现在精神活动中,还显现在日常生活中。而且精神上的与自然合一,仍然是通过在现实生活中融进自然完成的。他是“结庐在人境”,从“五柳先生”做起,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做“无怀氏之民”、“葛天氏之民”的乐趣,进入与自然合一的人生境界。从他讲“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可以看出他采取这种人生方式,完全是一种自觉行为。
陶渊明既然是在平凡的田园生活(包括躬耕)中达到与自然合一的人生境界,因而他的审美趣味,便带有崇尚真淳、平淡、朴质、自然的特点。
他的审美,是把自己融进自然,使之成为自然的一部分,用他的心灵、情感、意趣去感应自然、理解自然。于是他便能从极为平凡的景物、极为平常的生活细节中发现自然美和领会隐含其中的“真意(即自然意趣)”。而他的审美,重在会意、辨味、识趣。其审美标准、审美方式即整个审美趣味的形成,受到过儒学、道学、玄学审美观的影响,而以道学、玄学的影响最大。如道家以真淳为美、以自然为美,玄学以简约、平淡为美,以玄远为美和得意忘言的审美方法,都包含在渊明的审美趣味中。
陶渊明特有的审美趣味,既表现在他对历史人物的品评中,对理想社会的描述中,对人生境界的追求中,还表现在他对“奇文”的“欣赏”中,表现在他的创作理论和诗、文艺术风格中。

陶渊明的创作理论并不高深,他只是认为,文章是表述作者内心感受的,所谓“导达意气,其为文乎”(《感不遇赋序》)。感受要真实,表述要自然,“寄怀于言”(《九日闲居诗序》),一一从胸中流出。而作诗作文的目的是为了“自娱”,所谓“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饮酒诗序》),“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五柳先生传》)。既为自娱,当然容不得矫揉造作,更容不得假言假语,因为那是自歁。刘煕载说他讲的“示己志”“只是称心而言耳”,并不以“己志”“异人为尚”(《艺概·文概》)。刘氏所言,正好道出了渊明创作理论求真淳、尚自然的特点。
此外,陶渊明的创作理论,还深受玄学言不尽意论的影响。一方面,他主张寄意言外,即在平淡、自然的语句中注入深长、隽永的诗味、文旨,使人“开卷有得”(《与子俨等疏》)、有“意”可“会”,所谓“寄意一言外”(《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即如是;另一方面,他又说“言尽意不舒”(《赠羊长史》),隐含有言不尽意之慨,因而运用语言,赞成玄学家崇尚简约、质朴和不以种种修辞技巧(包括词采华美)力求“尽意”的做法。
正因为陶渊明胸次浩然,能进入与自然合一的人生境界,具有与其人生取向一致的审美趣味和创作理论,所以才有了与其人风相应的诗义、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