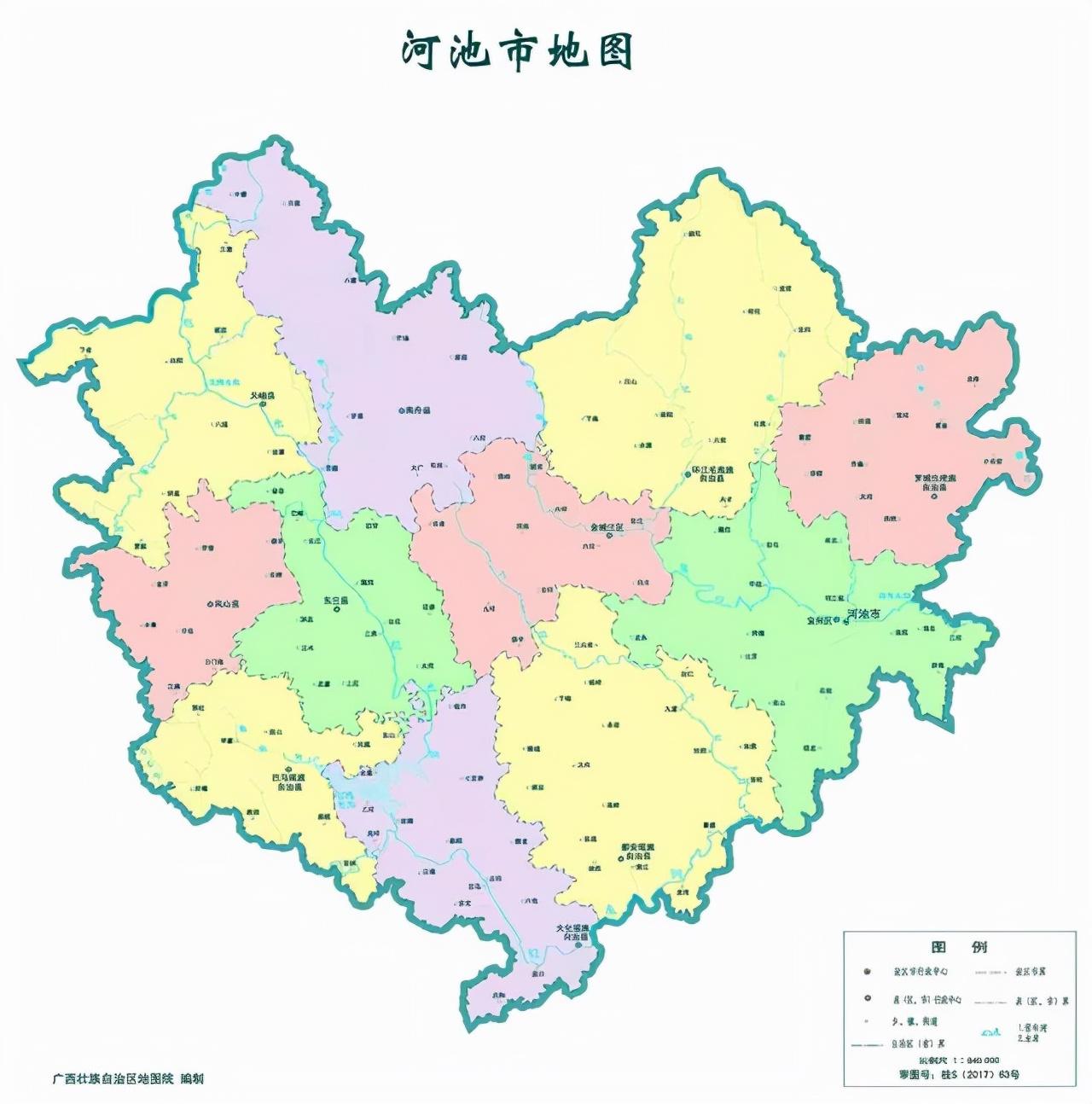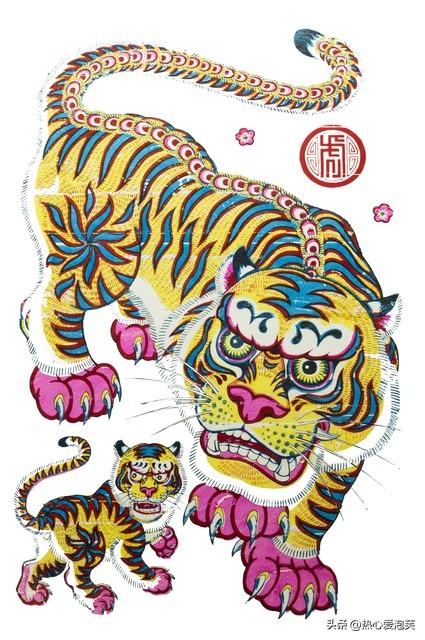2021年3月5日是波兰犹太革命家罗莎.卢森堡诞辰150周年纪念日。
1893年8月,当会议主席邀请她在第二国际苏黎世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言时,罗莎.卢森堡毫不犹豫地穿过了挤满整个大厅的代表和活动人士。她是在场的少数几个女人中的一员,还很年轻,身材矮小,臀部畸形,从五岁起就一直跛行。她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似乎是一个虚弱的个体。然而,她站在椅子上,以使自己更好地为人聆听,很快就用惊人的推理技巧和独创立场吸引了所有的观众。
她认为,波兰工人运动的中心诉求不应如许多人所坚持的那样,是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那时波兰仍处于三大帝国统治之下,由德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组成;事实证明,波兰的统一很难实现,工人们应该着眼于自身的需要进行实际斗争的目标。
在未来几年待发展的论点中,她批评那些专注于民族问题的人,并警告说,爱国主义言论可能被用来淡化阶级斗争,进而屏蔽社会问题的危险。她坦言,没有必要在无产阶级所遭受的一切形式的压迫中再增加一项“对波兰国家的屈从”。
不同流俗
苏黎世大会的介入,象征着一位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最重要人物之一的女性的知识传记的开启。150年前,1871年3月5日,卢森堡出生在俄属波兰,终其一生生活在边缘,与多重逆境搏斗,总是逆流而上。她是犹太人,身患终身残疾,27岁就迁往德国,通过一场伪造的婚姻在那里获得了公民身份,从事德占区波兰民族的工作。
一战爆发时,她坚定地奉行和平主义,因此几度入狱。在殖民扩张的新的暴力时期,她是帝国主义的狂热敌人,在野蛮中反对死刑,并且还是一个生活在几乎完全由男人统治的世界里的女人。
她几乎是苏黎世大学唯一的女性,1897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论述波兰的工业发展。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她被任命为中央干部学校教书的第一位女性,这是她在1907年至1914年间承担的一项任务。在此期间,她发表了名著《资本主义积累论》(1913年)并撰写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概论》(1925)。由此奠定了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上的地位。
她的独立精神和个性弥补了遭遇的困难--这一美德往往也会给左翼政党带来麻烦。活跃的思想,让她有能力在奥古斯特.贝贝尔和卡尔.考茨基这样的人物面前,不带敬畏地,甚至是令人宽慰地,为新思想的发展和创新提供动力 (这些党内权威曾享有与恩格斯直接接触的特权)。
罗莎.卢森堡的目的不是简单重复马克思的话,而是在新的时期解释这些话,继承的基础上还要发展。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对她来说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党员意味着拥有某些共同的基本原则,而党内就必须拥有不同观点共存的空间。
党,罢工,革命
卢森堡成功地克服了面临的许多障碍。在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的改良主义转变之后的激烈辩论中,她成为欧洲工人运动中的知名人物。卢森堡坚持认为,伯恩斯坦公开呼吁该党与过去擦肩而过,告别革命,转变为一支仅仅是渐进主义的力量。在《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1898-99年)中,卢森堡强调,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改良工作都是在上一次革命的推动下进行的。”
那些试图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鸟笼”中实现政治权力变革的人,并没有选择“一条更平静、更可靠、更慢的道路。”而是目标在变异,“他们接受了资产阶级世界及其意识形态。”重点不是改善现有的社会秩序,而是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例如,工会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会只能从老板那里获得更有利的条件--以及1905年的俄国革命,这些促使人们对可能导致社会彻底变革的可能主题和行动产生一些思考。
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1906年)中,卢森堡分析了1905年俄国革命的主要线索,强调了最广泛、大部分是无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关键作用。在她看来,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主角。在俄罗斯,“自发性因素”--这个概念导致一些人指责她高估了大众的阶级意识--是很重要的,因此,党的作用不应该是准备群众罢工,而应该是“指导整个运动”。
对卢森堡来说,群众罢工是“革命的活生生的脉搏”,同时也是“最强大的驱动轮”。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群众的运动方式,是革命中无产阶级斗争的现象形式”。这不是一次孤立的行动,而是长期阶级斗争的总和。
此外,不可忽视的是,“在革命的风暴中”,无产阶级被改造成“即使是最高的善、生活--更不用说表层的物质福利--与斗争的理想相比也没有什么价值”。工人们获得了阶级意识和政治成熟。俄国革命表明,在这一时期,“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相激荡”,其中一个可以立即进入另一个。
共产主义意味着自由与民主
在组织形式问题上,更具体地说,在党的作用问题上,卢森堡在卷入了另一场激烈的论争,这一次是与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立场进行了辩护,提出了党是职业革命家,是领导群众的先锋队的核心概念。
相比之下,卢森堡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4年),认为一个极端集中的政党促成了一种非常危险的“盲目服从中央权威”的状态。党不应扼杀而是要推动社会的参与,以实现“正确的斗争形式”。马克思曾经写道:“真正的运动的每一步要比几十个计划更重要。”卢森堡把这一观点扩展到“真正的革命劳工运动所犯的错误,在历史上比所有可能的中央委员会中最好的人的错误更富有成果,更有价值。”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这场冲突变得更加重要,她无条件地支持了这场革命。她对俄国正在发生的事件感到担忧(从解决土地改革的方式开始),她是共产党阵营中最早观察到“长期紧急状态”将对社会产生“有辱人格的影响”的人。
在狱中名作《论俄国革命》(1922[1918])中,她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是“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取代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是彻底消灭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进行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这并不是指望一位无懈可击的领导人来指导它。只有通过复杂的过程,才能达到真正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而不是“只为政府的支持者,只为一党的成员”保留自由的权利。
在《论俄国革命》稿的边页上,卢森堡加注道: 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 ”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它就不起作用了。
卢森堡坚信,“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是不可能自上而下的”,它必须扩大民主,而不是削弱民主。她写道:“消极的,撕毁的,可以通过法令的;积极的,建设的,则不能。”这是“新的领域”,只有“经验”才能“纠正和开辟新的道路”。斯巴达克派于1914年与社民党决裂后成立,后来成为德国共产党(KPD),该派明确表示,它永远不会接管政府权力,“除非是为了回应德国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群众的明确、确定的意愿”。
尽管相互反对,但社会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都错误地共享了民主和革命是非此即彼的两种选择。相反,卢森堡政治理论的核心是二者不可分割的统一。罗莎 47岁时在右翼准军事组织的控制下残忍杀害,她的政治遗产受到了两方面的挤压:社会民主党多年来一直与她斗争,片面放大了她思想革命性的一面,而斯大林主义者刻意保持沉默,避免她批判的、自由的锐利思想为更多人所熟知。
反对帝国主义和世界战争
反对帝国主义和世界战争,卢森堡政治信念和行动主义的另一重点。她证明有能力更新左派的理论方法,并在第二国际大会上赢得对反战决议的支持,这些决议虽然被忽视,但却是世界大战支持者的一根刺。
在她的分析中,军队的作用、重整军备和反复爆发的战争,不能仅用十九世纪政治思想的经典术语来理解。相反,他们与压制工人斗争的势力联系在一起,成为反动统治分裂工人阶级的有用工具。它们也符合这个时代精确的经济目标。
资本主义需要帝国主义和战争,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如此,以便增加生产,并在欧洲以外的殖民边缘地区占领新的市场。她在信中写道“政治暴力只不过是经济进程的一种工具”--这是她在《资本积累论》所作的判断,即重整军备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性扩张是不可或缺的。
这幅图景与乐观的改良期望相去甚远,卢森堡发出了一句在20世纪引起广泛共鸣的名言:“社会主义还是野蛮?”她解释说,只有通过自我意识的群众斗争才能避免第二个选项,而且,由于反军国主义需要高度的政治意识,她是反对战争--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其他人都低估了的武器--的最伟大的思想者之一。
她认为,国防的主题应该被用来对抗新的战争场景,以及“对战争的战争!”口号应该成为“工人阶级政治的基石”。她在《社会民主的危机》(1916),也称为尤里乌斯小册子分析到,第二国际组织之所以崩溃,是因为它未能“在所有国家实现无产阶级的共同策略和行动”。从那时起,无产阶级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与帝国主义作斗争,防止战争和反对战争”。
不会失去她的柔情
罗莎.卢森堡说,她是即将到来的世界公民,“在世界各地,哪里有云,哪里有鸟,哪里有人的眼泪”,她感到宾至如归。她对植物学充满热情,热爱动物,她在信中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女人,尽管她经历了痛苦的生活,但她仍然和自己在一起。
对于这位斯巴达克主义联盟的创始人来说,阶级斗争不仅仅是一个加薪的问题。她的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经济主义的。她沉浸在她那个时代的戏剧中,试图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而不对其基础提出质疑。她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不断向左翼发出警告,运动不能局限于平淡的渐进,不应放弃彻底改变现状的努力。
罗莎.卢森堡的生活方式,以及所阐述的民主社会主义理想,迄今依然是新一代激进分子向往的灯塔,人们继续追随她,并走在她曾走过的道路上。